

方立天說
「每當我看到觀音、關公這些塑像,就有一種異常神奇的感覺湧上心頭,引發出難以名狀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要『靜心專一』。雜念多不容易看好書,浮躁寫不出好東西,要甘於寂寞,坐冷板凳。」
「我把自己的任務限定為從學術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敘述和評價宗教的複雜現象,肯定在我看來應該肯定的東西,否定在我看來應該否定的東西。」
「天時、地利、人和,塑造了我的學術生涯,編織了我的人生。人生離不開緣,人生就是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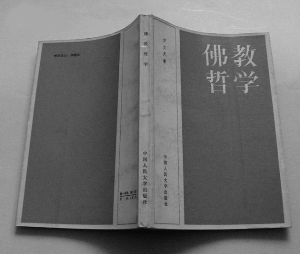
50載佛學人生
(文/中國教育報記者楊晨光)
他,是著作等身的大學教授,其著述代表了20世紀以來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是宗教學界的泰斗人物。國家宗教局局長在他面前自稱「學生」;佛教協會高僧面對他也以「晚輩」自居。
2011年,步入人生第78個年頭的方立天,迎來了他從教50周年的紀念。在中國人民大學為他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來自各大寺院的住持長老,各個宗教協會的領袖,佛學界、哲學界的知名人士一齊亮相,盛況空前。
眾星捧月中,這位享譽海內外的佛教學家、中國哲學史家和宗教學家依然低調而平靜。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起自己半個世紀的佛學人生,已近耄耋之年的方立天話語中依舊滿含禪機:「每個人的人生都與一定的因緣條件相依相存,互動互變,並在因果律的支配下展示其獨自的意義與價值。天地人和,因緣際會,成就了我的學術人生,構成了我的幸運人生。」
中國佛學院的「俗家弟子」
兩撇斑白的佛眉,頗有古拙之氣;說話語速很慢,但卻有條不紊。坐在沙發上的方立天,就好像冷清角落裡的一介學人,不溫不火,遺世而獨立。
方立天出生於浙東農村,他一直記得童年時學校後面的那座小小廟宇,觀音和關公共處一室。記得母親每日裡燒香拜佛,有時半夜叫他起床,走40多里山路去拜神,吃齋飯。「每當我看到這些塑像,就有一種異常神奇的感覺湧上心頭,引發出難以名狀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幼年時心靈埋下的種子,讓方立天後來報考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並如願以償。畢業時,中國人民大學到北大來要畢業生,挑了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各一人,其中學中國哲學的,挑的就是方立天。
說起如何走上佛學研究的道路,方立天記憶最深刻的就是在北京法源寺8個月的進修學習。「我應該是人大建校至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到寺廟裡學習過的教師。」談起那段經歷,方立天不無得意地說。
1961年,28歲的方立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擔任助教。當時教研室要教師們各自敲定研究領域,方立天挑選了無人認領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把自己的大好年華交代給了那段天下紛爭、佛教大興的歲月。
研究佛教,談何容易?在北大讀書期間,方立天只接觸過兩個課時的佛教學習。「光看書是不行的,必須要去聽課。」抱著這樣的想法,他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沒有一處開設佛學課。
當時,正是政治運動不息的年代,宗教領域受衝擊,被許多人認為是「敵對」的思想範圍,方立天卻認為,這是中國傳統的東西,應該有人去學。他到處打聽,終於得知佛教界自己辦了一所學校叫中國佛學院,就在位於宣武門的法源寺里,有出家人在傳授佛教課程。
法源寺是北京城內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古剎。1956年,以培養僧才為目標的高等佛教院校----中國佛學院在法源寺創辦,有來自全國各地寺廟的100多名學僧在此學習。其深厚的歷史底蘊和佛學傳承吸引了方立天。
在徵得哲學系以及教研室的同意之後,從1961年9月底開始,方立天每天換乘兩趟公車加步行,花費1個多小時的時間趕到法源寺旁聽佛學課,晚上再趕回學校。
於是,在滿屋僧侶的中國佛學院課堂上,出現了一個身穿中山裝的「俗家弟子」,他總是坐在最後一排,認真地記筆記,專注地聽講。
佛學院對於方立天這樣的「另類」出現懷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擔心他來學習是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覺得高校青年教師願意來寺學習,是學院的光榮。這樣「走讀」一段時間後,寒冷的冬天就要來了。「出家人真的是慈悲為懷。」方立天回憶說,「當時學院的副院長周叔迦大師看我每天跑來跑去很辛苦,怕我凍壞了,就允許我住到寺里。」
每天早上4點,僧人們起床做早課,方立天也起床讀書。與暮鼓晨鐘相伴,和出家僧徒朝夕相處,受教於一批一流佛教學者,接受了純正的佛學知識教育。尤其是副院長周叔迦,親自給方立天開書單,並讓他定期報告讀書心得,可謂耳提面命。
一住就是8個月,這段經歷對方立天影響很大。從那以後,他對佛教有了一個整體的了解,對僧徒的生活也有了感性的認識和理解。從此他寫文章,在當時的形勢下雖然還不免批判佛教,但講道理,不謾罵,也不全盤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這些都獲得了佛教界的認同。
從講師直接晉升為正教授
在「方立天教授從教5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向與會者講了一個故事。
2001年,剛剛調任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程天權一進學校,就聽說了這樣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人大復校之後,有一位教授背著黃書包到圖書館看書,從早上7點一直看到晚上7點,20多年如一日。後來圖書館專門給這位教授設了一張辦公桌,以免他和學生搶座。
「情節基本屬實。」故事的主人公方立天笑著說,「我不光拿著包,還經常帶著大茶杯和小水壺。到圖書館看書的習慣是我到人大工作後就開始的,一直到2005年我的住所搬到人大校外。還要強調一點,人大復校時,我還只是個講師,不是教授。」
1978年,人大復校,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別的校園。那一年,他45歲。
物是人非,這個時候的方立天已經不再是學術新秀。他已經是一雙兒女的父親,全家四口人蟄居在不足30平米的筒子樓里,工資入不敷出,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是講師。
然而這些不如意並沒有阻擋方立天的步伐。他沒有時間過多地感嘆生活的困窘,而是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節假日,背著書包和大學生一起走進圖書館,看書、備課、寫文章。「我在2006年前發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圖書館完成的。」
讀書人都知道,康德作息準時,他出門散步的時間可以供鄰居定時用。在人大校園裡,也有這樣一座鐘,那就是方立天進出圖書館的時間。他每天早上等著工作人員開門,晚上由工作人員催著「收工」。久而久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也被他感動了。那時的圖書館,書庫是封閉的,需要什麼書,得填寫書單,由工作人員提取。圖書館卻為方立天在書庫里設了專門的桌椅,他一伸手就可以從書架上取書。這樣一來,他真的被「埋」在書山書海里,可以「海闊憑魚躍」了。
這一時期佛教研究逐漸恢復,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和師友一起編輯了《中國佛教思想史料選編》4卷共10餘冊,成為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國內最流行的佛教資料集。他自己則撰寫了《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得到了時任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出版小組組長李一氓的高度評價,將其稱作古籍整理的典範。
1983年,人大進行職稱評定。方立天提出了一些建議,希望讓職稱評定更加規範。「這下捅了『馬蜂窩』,本來聽說我在副教授的評定中排在前列,但後來名單公布時把我拿掉了,領導找我談話說起沒有評我的原因時也是含糊其辭。」
在一些人看來,遭此打擊的方立天可能會消極罷工,也可能尋求調動工作,甚至還可能跳樓自殺。
或許正是佛教賦予的智慧,柔軟又堅強。方立天並不與現實世界擰著來,但也絕不無條件地順從形勢而墮落。他生性沉靜寡言,但心裡有主見,認定的事堅持不動搖。
「雖然內心感到不公平,但我覺得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還是要有真才實學,把課上好,把科研搞好。」帶著這樣的想法,第二天,方立天照常背著書包走進了圖書館。
正所謂天道酬勤。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部分重點大學的文科類專業中選拔一批年輕一點的正教授,推動青年人才的湧現,哲學學科全國一共要評5個。經學校推薦、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審定,方立天從講師直接晉升為正教授。那一年,他50歲。
兩年後,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學》。該書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最廣的一本佛教入門書,許多這一年代成長起來的佛學專家和高僧都不諱言此書的入門之功。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稱讚說,中國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門書」。
曾任馮友蘭的課代表
如果從1956年方立天進入北大哲學系讀書算起,他和中國哲學打交道已半個多世紀。迄今為止,他出版專著15部,合著18部,發表論文360多篇,培養了40餘名碩士與博士研究生,如今絕大部分是教授。
「學生不是來給老師打工的。」方立天語出驚人,談起如今一些導師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的現象,他極為憤慨。「我從來不給學生制定論文選題,也不把自己課題的一部分給學生做,而是指導他們獨立思考,從興趣出發做論文。」
研究佛教之難,非身體力行者不能體會。佛經難讀,卷帙浩繁,讓人頭疼。有學生請教方立天研究佛經的捷徑,方立天給了個最笨的辦法:反覆看。「一本《肇論》我曾經看了幾十遍,才漸漸有所體悟。」
「立身有道,學有專長」,這是方立天的座右銘。「其實,這都是恩師馮友蘭對我的影響,他才是真正的泰斗。」
未名湖畔的5年學習,方立天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當時的北大,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們都還在,哲學系裡的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任繼愈等人都還站在講台上,這些學者無一不是學貫中西的大家。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魚得水。
作為中國哲學史課的課代表,方立天與授課教師馮友蘭有了更多的交往機會。每堂課後,方立天都要蒐集一些同學對課程提出的問題,然後到馮友蘭家裡轉交。「師母特別客氣,經常拿糖果招待我,吃得我滿口留香。」「馮友蘭先生講話有些口吃,但幽默風趣、邏輯性強,尤其文字表達能力更是厲害。」
在聽了馮友蘭幾個月課之後,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馮友蘭的教學工作被停止,方立天和他的同學們成了馮友蘭親自上課的最後一批本科生。
在先哲的帶領下感悟學術,並受到純正學術路數的薰陶和浸染,「修辭立其誠」、「靜心專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成為方立天一以貫之的治學方法和態度。「這是我的老師對我的影響,我再把這些治學原則傳承給我的學生,為他們學術研究的成功打開登堂入室的大門。
「『修辭立其誠』就是講話、發言、寫文章、治學都應堅持真實性。」方立天的弟子、人大哲學院副院長魏德東說:「老師的治學原則說得通俗一些,就是誠實做學問,把讀書和做人結合起來,維護學者的獨立人格。在學風和社會風氣追逐淺薄浮躁的當下,老師的要求能幫助我們立身有道、自尊自強。」
拒絕急功近利,學術思想才能與時俱進。經過前後15年的寫作,2002年,方立天完成91萬字的巨著《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在學術界、佛教界、政界引起巨大反響,被譽為現代佛教哲學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
時任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佛學家任繼愈先生為該書題字「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形象地反映了方立天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目標一經確定,就終身追求、矢志不渝的信念。
「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精思窮微著作傳九州」,國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以這副對聯精闢概括了海內外學術界對方立天取得成就的一致公認。
9月17日,在方立天教授從教5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場,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手捧一面銀光閃閃的錫盤,上面刻著「道德文章,為人師表」8個大字,送到方立天手中。王作安感慨地說:「宗教局這幾年延攬了不少方先生的弟子,他們都已經成為推動國家宗教事業發展的中堅力量,我要代表他們向方先生的辛勤培育表示感謝。」
宗教是文化而非鴉片
今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國務院小禮堂主持國務院參事、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會。身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方立天教授在會上作了「科學認識宗教的本質與功能,提高宗教工作水準」的專題報告。
「2008年的五四青年節,總理來到中國人民大學看望青年學子時,我有幸見到了總理,當時總理對我說『佛教文化是可以交流的』,這句話給我留下了親切、難忘的記憶。」這次會上,方立天懇切地指出,目前宗教方面存在的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宗教鴉片論」尚未真正澄清,以致在觀念上和行動上形成一些偏差。
「我在會上一再強調,宗教的本質是文化,是信仰性的文化,宗教是一種社會文化體系,是人們的一種精神生活方式。我的發言得到了總理的肯定。」方立天回憶道,開完會,總理專門走到他面前說,「您說的宗教是文化,沒有錯」。
雖終日埋首於圖書館,方立天的研究卻無時不關注著時代的風雲。
自2004年開始,方立天主持的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創辦了「中日佛學會議」,每兩年一次邀請兩國頂級佛教學者就雙方共同關心的主題展開討論,以延續一千多年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慧命。
----日本創價大學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長菅野博史說,通過對話交流,兩國宗教界探討了如何承擔起對各自信徒的教育責任,從而廣泛發揮宗教的影響力,促進人類對所面臨問題的解決。
中央統戰部與中國人民大學合作開設愛國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方立天每期都要參加研修班的開班儀式,並親自為研修班學員授課。
----參加過第4期愛國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浙江省佛教協會會長釋怡藏,在聽了方立天的講座後說:「方教授大聲疾呼,更好地挖掘整理、詮釋發揚中國佛學的精華,為構建當代世界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是今日我們宗教學者的重要責任。學者們尚有這樣的責任和志向,更何況我們這些佛教界人士?」
基於對宗教學理論、宗教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方立天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教工作方針政策的貫徹與完善,宗教領域重大現實問題的認識與處理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說:「方立天先生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學者,他的卓著成就足以矗立在學術研究的光榮史冊上。」
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種忠誠與智慧卻足以推動事業的長遠進步。
2000年,方立天出任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引入一流人才,培養年輕學者,如今,研究所已從建立時的5人發展到擁有專兼職研究人員20人,其中75%是教授,成為被海內外公認的代表國內最高水準的佛教與宗教學研究機構。2003年,他主編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目前已成為反映國內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園地。
然而,方立天牽掛的事還有很多。
----有的學生考上了宗教學系的本科生,卻被家裡人阻止不讓上,「說明還有很多人把學宗教、研究宗教視為『異類』,在全社會形成尊重宗教的氛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方立天經常在作報告或公共場合講話時,呼籲大家不要給宗教扣上帽子,要用正確的心態看待宗教。
----每逢有政府領導出席的活動,方立天都會直言不諱:宗教在加強道德建設等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能夠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憂之切,因為愛之深;愛之深,所以盼之切。如今,78歲的老人將學術重心轉向中國儒釋道三者關係的研究,期望以此把握中國文化的特質,並為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作出自己的思考。
「我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觀的研究者。」方立天最欣賞「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這句古訓。「治學要有正確的立場,維護自己的人格,言論不能譁眾取寵,也不能故弄玄虛。」
雖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認,佛教義理探討安身立命之道,凝結古人深層智慧,對他的生活和思想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的工作、事業取儒家態度,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則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順其自然,淡然處之,追求一種精神價值,這也是一種不爭而爭吧。」
清水下的三顆「雨花石」
(文/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哲學院教授何光滬)
方立天老師平日同我的交往,真的是「淡如水」,但在我心中,這一泓清水的底下,卻沉積著三顆小小的「雨花石」,那上面刻的是「欽佩」、「感謝」和「學習」。
近些年來,方老師可謂聲譽日隆,不過我們應該都記得方老師幾十年前的境遇,那恰如陸游所詠之梅:「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我至今記得,1989年6月3日晚,我送兩冊博士論文到他在人民大學「靜園」的家中,眼見這位我很欽佩的老師住在狹窄、陰濕、昏暗的斗室,心中真不是滋味。當然,在那些年裡,中國絕大部分大學教授的生活狀態都是如此,大家也司空見慣。
在那個年代,尤其是經過「文革」破「四舊」、「狠批封資修」的暴風驟雨,在當時被稱為中國「第二黨校」的中國人民大學,鑽研被稱為「唯心主義」、「封建迷信」的佛教,一般人很難理解方老師的研究。然而方老師依然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用一副弱小的身軀和一顆堅韌的匠心,去鏤刻那佛學的堅硬金石,終於完成了置於大家案頭的如許學術精品,這實在令人不能不從心底欽佩!
方老師還是一個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的生活更有意義的人。其實,我在17歲時就下鄉當民辦教師,20歲時再次下鄉在國小任教;後來返城,又在不同的中學教不同的科目;甚至讀大學本科時也在醫學院任教,碩士畢業後又任教;攻讀博士時,在中國文化書院、魯迅文學院、北京大學等處講課。總之,我似乎與教書這一行天生有緣。但是,在取得博士學位以後,儘管偶爾應邀講講課,卻因為天性不好動,又因為喜歡自己的專業,我在中國社科院宗教所,埋頭一乾就是12年。
2000年夏,方立天老師找到我,鄭重邀請我來人民大學任教。他當然說到了教書育人對培養學科後來人的重大意義,而且還說到教育部批准人民大學成立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基地,必須要有佛教和宗教學理論兩個方面的學科人才。他的坦誠令我感動,「教書育人」也令我心動,但我並未立即答應調動,而是猶豫了一年多。直接的原因,是我覺得與社科院的同事相處得不錯,不好意思提出離開;深層的原因,是自己生性懶惰又兼「完美主義」,做事太慢而有「文債」壓力,所以害怕「教書育人」再增添時間壓力和精神壓力。就這樣,又想教書,又怕教書,「利」亦在此,「弊」亦在此,由於委決不下,就用別的一些理由來推託。不料,2001年夏,在我去香港做訪問教授而逃避抉擇期間,碰巧方老師也到香港做訪問教授。方老師專門找我和夫人長談,徹底打消了我的顧慮。於是,在2001年秋,我終於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走進了中國人民大學----就我而言,從閉目塞聽的象牙塔,走向生氣勃勃的大學生,壓力很大,意義更大。為了終於走回這條我天生應該走的道路,我要永遠感謝方老師!
到人大整整10年了,對方老師有了更多的了解。以我的感受而言,除了行事低調、待人誠懇、腳踏實地、慎言篤行等大家熟悉的特點,方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品格,是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和虛懷若谷的開放心態,這恰恰是當代學者最需要的品格。
眾所周知,方老師多年的佛教研究和中國哲學研究,都是以詳細、大量地占有資料為基礎,言必有據,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不發那種不顧事實的高論,也不寫那類無法論證的虛言。正因為堅持了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才有了真正虛懷若谷的開放心態。他的虛心不是外表的「謙虛」,而是對自己之強弱、長短、優劣的真正意識,對自己研究領域、局限、界線的真正意識。他的開放心態,來自他對社會現實實事求是的直接面對,對文化危機實事求是的憂患意識。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在當年邀請我來人民大學時坦誠直言,除了佛教研究人才以外,研究所還需要宗教學理論人才;他才會在不久前論及社會上對宗教的過時認識時,不諱言宗教政策方面的問題;他才會在一個滿座高官耆儒的會場上,作為一位佛學老專家而坦言對基督教應該抱一種開放的心態。
所有這些,都來自方老師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虛懷若谷的開放心態。想到這些,我必須說,在方老師從教50周年之際,我的心裡不僅有欽佩和感激之情,也有向他學習、以他自勉的願望。
本文原載2011年11月4日《中國教育報》,為緬懷方立天教授而重新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