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的軌道時有變化,這種變化有時就決定於一悟的一念之中。一代高僧能海法師就是從馳騁疆場的威武軍官,而成為吃齋念經的佛門弟子,從而走完了一條獨特的人生之路。
能海法師俗名龔緝熙,四川綿竹人。1886年臘月22日生於綿竹漢旺場。父親名常一,母親張氏。他十多歲時,父親送他到北門大街的鐘姓綢緞鋪當學徒。父母在他十四歲時去世,能海法師靠姐姐為生,嘗盡了生活的艱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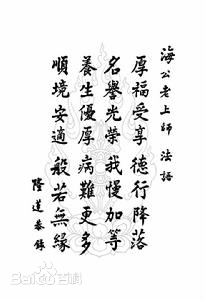
庚子之亂後,清政府日益腐敗,列強加緊瓜分中國。能海法師正值青春年少,血氣方剛。於是棄學從戎,考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在學堂中法師刻苦攻讀,成績優異。畢業後被派赴康定任偵察大隊長,不到一年,就升任營長。1909年,能海法師派到雲南講武堂任教練官。當時朱德在該堂求學,解放後,能海法師在北京又見到了朱德總司令。
1911年武昌起義後,四川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四川的政局非常動盪,政府也不斷更迭。能海法師隨著援川部隊由雲南回到四川,任第四鎮管帶(營長),在成都駐防,後任團長兼川北清鄉司令。
191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能海法師在成都的提督街之義廟聽佛源法師講經,大為醉心,於是就拜在佛源法師名下為弟子,開始對佛法感興趣,熱心地研習,此事就成為他日後皈依佛門的因緣。當時,四川軍閥混戰,全川戰火紛飛,人民在戰亂中受盡苦難。可是軍閥只想擴大自己的地盤,擴充實力,互相殘殺、吞併。劉湘在混戰中一升再升,由營長升為軍長,以至川軍的前敵總司令。為了鞏固自己的基礎,把原來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的同學儘量招納進來委以重任,能海法師也屬於招納之列。此時的能海法師已開始相信佛法,不願當官帶兵,只擔任幕僚的職務。劉湘經常派他到各地周旋,所以,他得於常常奔波於北京、天津、上海、武漢、重慶之間。1915年他東渡日本,考察那裡的政治與實業,同時有感於日本的佛教非常盛行。於是在回國後,每到一處總是竭誠訪求明師,研習佛法。他還曾經求教於北京大學的哲學教授、佛學家張克誠先生,他不顧路途遙遠,每天往返40里,不辭勞苦。1921年以後,他辭去外務,在成都山城公園辦「佛經流通處」。1924年,他終於拋棄紅塵中的一切,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取法名「能海」,剃度後即到新都寶光寺從貫一老和尚受具足戒,當時39歲。
能海法師由軍官而佛門弟子,其人生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做此選擇,是他在閱盡了人事滄桑以後,感到「五蘊皆空」。他早年加入過同盟會,對國民黨比較同情,積極投身革命。後川軍中擁護袁世凱的將領對各地國民黨人及參加和回響討袁的起義人士,進行了極其殘酷的鎮壓,同學中除劉湘一人立功升官之外,同情起義軍的被殺了許多。能海法師看到昔日同學慘遭殺戮,血流成河,內心非常悲痛。此外,他還遭到了家庭的不幸,厄運連連。他的元配夫人莊氏早逝,留下一女。後娶張氏,又娶張氏的妹妹,生下一子,和他的感情很好。沒想到後來妻妹也一病不起,這使法師極度傷感,頓感人生幻化無常,想到了以前修習的佛家妙旨,便萌發了剃度出家之念,「度一切苦厄」發心向佛,解脫內心苦惱的羈絆,在佛門中尋個永久的清淨之地。
法師在受具足戒後,在金光寺住了幾個月,一面學習戒律及禪教諸宗,一面又準備到西藏學法。後來到康定跑馬山的喇嘛廟住了大約三年,潛心學習藏文藏語,1928年5月,帶著準備好的禮物十幾馱,進藏學法,歷時四個月,旅途備嘗艱辛,於9月抵達拉薩。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薩門下為弟子,在藏學習約十年之久,學習成績優異。康薩對能海法師戒行精進,尤為讚賞,把自己用的衣、缽和許多珍貴經典交給能海,康薩己認定能海是繼承他法流的承傳弟子了。1936年,能海法師取道尼泊爾、印度,乘海輪迴到祖國,他先在上海講經,後來又到五台山廣濟寺閉關修習佛法。出關後不斷從事譯述,為弘法做準備,並在上海、太原多次講經。「七七」事變以後,能海法師率領弟子20餘人返回四川,成都文殊院的法光和尚請他住在南郊的近慈寺。該寺為文殊院的下院,年久失修。法師在這裡住下以後,不但恢復了舊觀,還先後建成威德殿、大師殿、藏經棒、沙彌堂、譯經院、金剛院、方丈寮等建築。就是在這裡,能海法師開辦了內地第一個密宗道場。國內各寺院的僧人聞風前來學習的有許多,當時的許多軍政要員、在家居士,都前來聽講經說法。能海法師講經,教理圓融,辯才無礙,且深入淺出,妙喻橫生,信手拈來,皆成妙諦,故能攝引上中下之根各得趣味。所以,聽眾非常踴躍。
能海法師難得在修行的過程中,有毅力,不放逸、嚴守戒律,過午不食。他還堅持素食,早在西藏求學之時,其行為就曾感動過西藏的僧眾。當時西藏出家為僧的人,無論地位如何,對於肉食都很隨便,而能海法師卻堅持不吃肉,當地僧眾對此非常驚嘆,說:「能海對肉一點都不吃,簡直是個活佛了。」他每天的飲食起居非常有規律,每天早晨3點鐘便到大殿上座,開始講經,或在講經前先講一些寺內事務,約兩小時講完,下座後進早餐。上午9時至11時又上座講經,12時前進午餐,午餐後是會客時間,下午有時也講兩個鐘頭經,不講經則譯經或靜坐。傍晚有時同居士們在寺內園林中散步談天,前半夜又靜坐。一晝夜間在榻上時除靜坐修正觀以外,如微有倦意,也只是盤腿靠靠,絕不倒頭大睡,多年堅持如一日,法力是非常驚人的。而且他每年夏天都去綿竹的雲霧寺靜坐,他靜坐的地方是另修的茅蓬,是功夫高的人才能去的地方。因為靜坐並不是簡單的事,而是按功夫深淺分為幾個等級。
能海法師在住持近慈寺時,繼承叢林制,吸黃教的寺廟家風,上殿念誦,用漢譯藏文儀軌,中間加進誦漢文《大般若》、《華嚴》等大乘經典。沙彌堂培養青年,既學佛學,也學文化及藏語,並迎來五台山扎薩喇嘛教辯論。法師對於弟子的教育,是戒、定、慧三學並進,特嚴於戒學。近慈寺雖為密宗,但它的教規非常嚴格,所以稱之為律宗亦不為過。他為寺里的僧眾定下了嚴格的紀律。寺僧不赴經懺,但每日須誦經四座,寒暑無間,而且還嚴格限定女眾進寺離寺的時間,上午必在8時以後,下午離寺必在4時以前。如逢法會,女眾隨眾念誦聽經,不得串寮。縫紉洗濯之事,比丘自己為之,不能讓女眾代替。女眾住的地方,必須離寺5里以外,而且寺僧沒有事情不去俗人家,有事必須去也得兩人以上同行;沒有必要的話不得進入門內,只能在門外站著說話,不是有公務在身,不得隨便進入街市。能海法師曾經說過:「人不會做事,必不會修行,如何能成佛?」以此可以看出,他從最簡單的做人道理入手深入到佛法的真諦。平常僧衣法服,供品糕餅,都是寺里的僧人自制。耕種園藝,植樹造林,都是僧眾在誦經之餘,人各專其事而完成的。近慈寺特設學事堂,入寺必先學事。
能海法師曾經說過:「行般若道,行下士行,」即謂見地要高,行履要實,不能徒尚玄談,無補實踐。想法師當初在軍旅中供職,若無意於佛門,前途定也無量。但法師有意於諸行無常之苦,故發心托跡空門,斷絕一切塵念,這實為尋常人所難下的決心。而一旦成為佛子,又帶佛門戒規嚴於律己,精進不懈,所以,觀法師其人之言行,確存有正知、正見,因此,見地頗高,能發起正行。他自己,不但能依循這種見解行事,而且還諄諄教導皈依在他座下的弟子們。身教重於言教,正因為能海法師對於佛教的研習深得其中機趣,對於時局政務亦能有很正確的見解,絕不流於媚俗,隨波逐流,以圖謀虛榮,故對名利也能淡然處之。法師為法亦為人,不愧為一代高僧。他之所以成為人們宗仰的楷模,絕不僅僅在於對佛教的貢獻,在做人上也是值得稱道的。
法師嚴守佛制。1949年夏,峨山磚殿修復,法師率弟子到新修的慈聖庵安居,為普賢銅像裝藏。法師先回成都,兩位上座僧人後來隨某軍人夫人的車回到成都。為此,他們受到法師嚴厲的批評和處分,其中一人,還被遣送到綿竹縣西山雲霧寺靜座,不準出山。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從上海來到近慈寺,對大夥說:「共產黨要消滅宗教。」法師知道後,立刻叫當事人把他趕走了。還有一次,法師在彭縣修舍利模型塔,當時彭縣一帶住著起義軍,以及一些進步人士和共產黨的代表。縣城裡顯得十分平靜,人們很高興。法師和一些僧人也在議論解放的事。就在此時,監工修塔的僧人跑來對法師說:「趕快把塔頂安上吧,不然共產黨來了……」沒等他把話說完,法師就生氣地說:「來了怎麼樣,中國人嘛,不是外國人!」法師雖為出家人,但其身為並不拘泥於不問人情事理,崇尚玄談,而是救人於危難之中,充分體現佛的大悲大勇。
能海法師說法40年,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致函請往弘法,法師婉辭未赴。林森親題護國金剛道場匾額,法師對此漠然視之。蔣介石政府請法師出任參政員及「陪都宗教聯誼會」顧問,法師一一予以謝絕。他自己說:「我不過是一個膽小的出家人」「但愛戒之心,可質之諸佛而無愧。」這些行為對於弟子的教育及影響無疑都是很大的。
法師顯密雙弘,不存門戶之見,法師為力挽盲修瞎煉的流弊,極力提倡講學,為力挽徒尚玄談之流弊,法師主張僧眾之學,必依叢林,才能付之於實踐。修必依學,不可盲人瞎馬;學必有修,不能說食數寶。法師對於密學,認為是與顯教相表里,相輔翼,亦是獨闢蹊徑,於佛教由顯教大乘而入密,由密而上溯根本乘原始佛教。法師在教弟子學法之時,也是由淺入深,執簡馭繁,且循序漸進,條理井然。這與他所主張的不流於玄談有關。說法必須使聽者明於精奧的佛理,得正知見,倘若只是為談而談,那是於事無補的。
法師對於拯救名山大寺文物,終生奔走,不遺餘力。彭縣龍興塔,建於梁代,後遭毀壞,法師發起修復,在彭縣開窯燒磚,仿印度菩提道場塔形,先建模型塔,高一丈余。峨山磚殿在火中焚毀,法師命令弟子普超籌劃修復。1949年夏天,法師又率領弟子到峨山慈聖庵安居,為普賢銅像裝藏;又於慈聖庵足盧佛脫沙像,擬建為專修毗盧儀軌道場。法師先後在成都近慈寺、重慶真武山、綿竹雲霧寺、峨眉慈聖庵、五台山清涼橋及上海金剛道揚,共開建道場六處,譯述及講稿共70餘種。
1966年「文革」開始,法師也未能倖免,移居到廣濟茅蓬,參加集體勞動。法師由於平時對於佛法的修習,相信善惡有報,故橫逆到來之時,能不失常度。這年的12月31日,法師象平時一樣和眾人一起學習。半夜起來登廁,遇到僧人成宗,法師讓他第二日代為請假。次日早晨,鄰單原寶光寺方丈妙輪喊師傅起來進早餐,不見應聲。看到法師面向西躺著,已圓寂了。法師世壽81,僧齡43,遺骨塔於善財洞旁邊寶塔山麓,來往的行人還能經常望見。